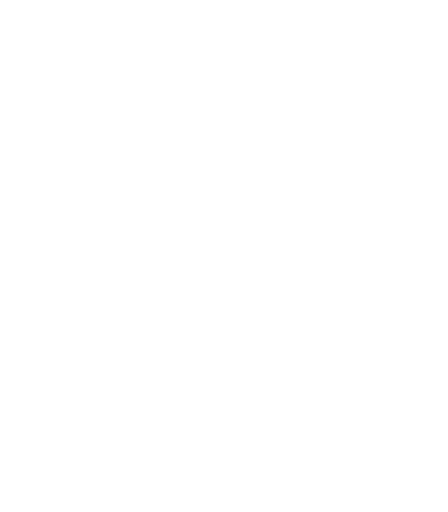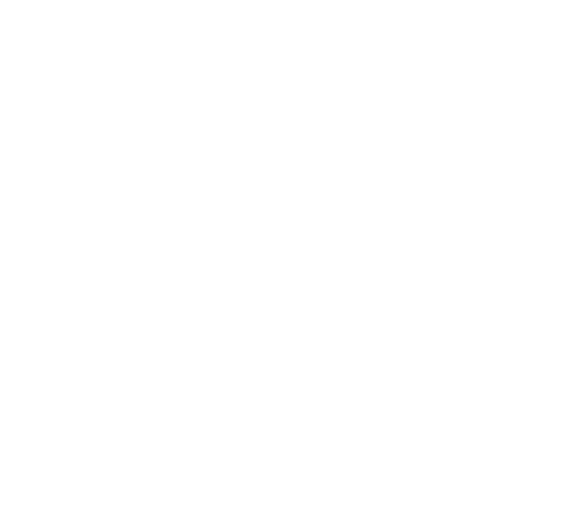施威全/淡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
英國國會為了行使其職權,可以處罰國會議員與平民,當議員或平民干擾大會或委員會的議事,構成藐視國會,國會有法律權力以及君主賦予的特權:警告、驅逐、罰錢、監禁議員或平民。
為執行立法功能、落實責任政治,英國的上議院、下議院經常性地授權各委員會行使國會職權,包括傳喚個人(persons)、書面(papers)與紀錄(records),俗稱國會的PPR權力,被傳喚者須遵從。被傳喚的對象拒絕出席國會作證時,下議會侍衛長得扮演拘令官,帶著象徵議會權力的權杖做為令狀,強制個人出席國會聽證。這時候侍衛長不是司法體系的法警,也不是行政體系的警察,但與法警、警察一樣得行使某種程度的強制力,也可以要求警察協助行使其職權。當權杖這個物體逐漸只剩下儀式性的功能時,例如用來敲開上議院的門啟動開議儀式,書面令狀就取代了權杖。
國會傳喚的權力大,甚至可以要求律師提供其客戶的資料,儘管這些資料受到「律師─客戶保密特權」的保護,在英國稱為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 (LPP)。例如2010年時下議院的文化、媒體與運動委員會就傳喚Harbottle & Lewis 律師事務所提供其客戶資料,這涉及到國際新聞界的一個大案子,梅鐸集團旗下的《世界新聞》非法竊聽失蹤少女米莉・道勒及其家人的電話,干擾警方破案,梅鐸本人被傳喚、出席委員會,《世界新聞》委任的律師也得交出與本案有關的資料。
國會行使立法、聽證、調查,媒體大亨、律師、官員、國會議員得配合,因為國會擁有處罰的權力,包括罰錢、監禁當事人等。儘管強制性的手段非常罕見,國會取得證詞、證物通常都是以協商的手法,施以政治壓力,期待當事人「自願」配合,若不是國會擁有最後的脅迫力量,不可能讓當事人「自願」配合國會行使立法、聽證、調查等權力。
國會可以發出拘禁、強制傳喚甚至處罰、監押議員、官員與平民,只為了行使國會職權,這倒底有無正當性?是不是混淆了立法與司法的角色?
一、正當性:就如法庭開庭時,法官認為律師、當事人乃至觀眾藐視法庭、干擾審判,法官得以處罰上述人等,甚至要求法警逮捕監禁。法官如此做,為了確保法庭程序,法警雖不是行政權體系下的警察,但仍然得以執行逮捕;國會執行處罰是同樣的概念。
二、立法與司法的角色分際:英國國會此般權力源自普通法,司法系統並不挑戰國會此權力,國會沒有侵犯司法權的問題。三權分立是簡化了的憲政原則,實際上三權的關係常有所重疊,法警涉及法庭事務時擁有與行政體系警察類似的權力,同樣的,下議院的侍衛長以及代理人也是。三權相互重疊最簡單的例子:雖然普通法的核心基礎是對私人財產權的保障,以穩固資本主義既定的生產關係,但在普通法體系下,不只是司法體系可用判決剝奪財產權,行政體系也可以逕行執行,例如罰款、限制建蔽率等。英國行政法體系建立在法庭判例以及成文法的基礎上,行政體系的剝奪財產權措施不等於侵犯了司法權,同時行政決定必須面對司法審查。三權的關係並非涇渭分明,國會的某些罕見作為,與司法權重疊但不算侵犯司法權。
以上是憲政的運作基礎,國會若成為沒有利牙的老虎,國會調查權就是虛的。
日前憲法法庭針對立法院改革法案的判決,就是拔掉立法院的牙齒,大法官們限縮了立法院職權,把立法─行政的關係推論到行政權獨大、不受立法院依法克責的極致。在【113年憲判字第9號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案】判決,大法官如此為文:
「於立法院受質詢且有答詢義務之行政首長、…應邀至委員會備詢,並負有說明義務之政府人員,抑或於立法院調查委員會之調查(聽證)程序為證言之政府人員,其於立法院為答詢、說明或陳述證言等,均係基於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前提,而負民主責任政治所要求之政治責任,亦僅負有政治責任,非法律責任。」
大法官們還強調:「行政首長或政府人員於立法院之陳述內容,涉有虛偽陳述致引發爭議者,乃屬政治性爭議,其本人自應受到民主問責,最嚴重之情形,即為去職以示負責。且如為虛偽陳述之政府人員為政務官時,其所屬政黨亦可能一併受民意之臧否與問責,乃民主政治運作之政治責任主要表現方式。」
意思是官員備詢、出席聽證調查,只是政治責任,不是法律責任;在立法院說謊也沒有法律責任,因此官員在立院所有言行都沒有法律後果,都只能訴諸輿論讓人民評論。大法官們把「責任政治」限縮為只剩下「政治責任」,否定了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互動、權限分際的基本法治,這等於宣判,在責任政治這題目下,立法委員的權力跟常人的自媒體沒兩樣,只能訴諸輿論狗吠火車而已。
關於國會調查權,原本國會改革法案裡的處罰機制,設計精神是「非不得以才用之」,實務上必須經過幾層程序根本難執行,但其存在是國會的最後籌碼。大法官可以質疑其設計不周延,或者認定其處罰規定是以牛刀殺雞、違反「合理性原則」,但不該完全拔掉立院的強制力,讓調查權淪為「只有開會的形式,無法實際調查」。
.jpg)